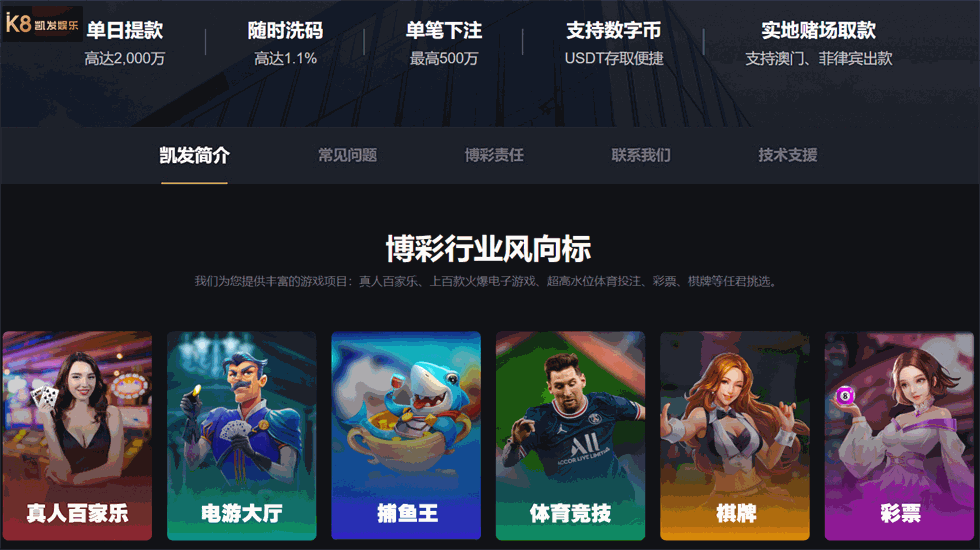我那赌了一辈子的舅舅不知道输了多少钱如今老了
发布日期:2022-02-27 18:56 点击次数:167

他非常能干,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那些年代为了吃饱肚子经常上山砍伐出大力气。他喜欢中国历史,时事政治他都很精通,经常用他那特有的夹带一点山东口音的东北话讲给我们听。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姥姥姥爷对他格外偏爱,尽管是老大,可他更像家里最小的宝贝疙瘩,下面的四个妹妹存在感很低,从我记事儿后我妈以及三个姨都对这个唯一的亲哥掏心掏肺的好,每到逢年过节,即使自己家过得十分艰难,也要尽其所能的给姥姥姥爷送去年节的礼物,因为舅舅和他们一起过,所以很多都不舍得买给自家孩子吃的点心水果都添呼了她们的两个大侄子(舅舅两个儿子)。
可能就是这些原因,导致我的舅舅一辈子没有脱离赌博这一习性,死性不改,除了赌博这一件事,他还真是一个优秀的老农民博彩问答,因为太讲武德博彩问答,以至于所有认识他的赌徒们都喜欢叫他上牌桌。东北有一种堵法叫做推牌九,具体玩法不懂,就是知道一晚上输赢个几千几万都是正常的,这对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是现在的农村来说可能是一个农民一年的收成。所以很多时候我舅舅都是输光了自己带去的钱后,那些人会非常主动的借钱给他,他们从不怀疑舅舅的人品,只要是自己的赌债,卖血他都会还,也是因为这样,我妈和姨们都十分痛恨那些把钱借给舅舅的人。
舅舅种了很多地,非常能干,那时候农业劳动基本靠人力,没有机械化,春种夏耕秋收,除了牛就是人,劳累非常,舅舅有个好体格,干活特别快,年复一年,每到秋天收回粮食卖了钱,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用来还他上一年冬天欠下的赌债,然后继续接下来漫长冬天的新一轮赌博,年复一年,年年如此,令人痛心疾首。

而我的舅妈,也是个奇葩一样的存在,她的面相看上去就会有个词从脑子里蹦出来:“尖酸刻薄”!家务活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农活勉强做一点,却长了一张说话难听的嘴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废话一堆一句有用的没有,舅舅不听她的,两个儿子,也教育得一踏糊涂,从小恃宠而骄,以至于现在,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弟,十几年了在外面混的水档尿裤,小儿子一家用尽了手段把家产耕地占尽了之后将父母弃之不管。
舅舅的赌博,成了笼罩在这个家族头上的一片阴影,挥之不去,记忆里的每年冬天,就是我她们姐妹几个和舅舅吵架,劝阻,满村子赌场找人的戏码,为了维持这个家,她们会不顾脸面去赌场骂那些借给舅舅钱的人,舅舅就反过来和亲妹妹们吵架。姥爷整日醉醺醺的,偶尔也会出来打听着找,而这时把门望风的早就通风报信,所以能找到人的时候很有限,偶尔找到赌场上的舅舅时,他却像换了个人换了个面孔一样,连姥爷也骂,现在回想起那些时候的日子,真是鸡飞狗跳,心惊胆战,令人不堪回首。
就这样,这个家磕磕绊绊的走到现在,姥姥姥爷相继去世,舅舅也成了七十来岁的老头儿,去年经历了一场劫难,给小儿子家帮忙收庄稼,被打苞米的机器砸到了身上,差一点没了性命,小肠被剪掉了一节,总算保住了命 。他身体底子好,加上我姨妈们的精心伺候,恢复的很快,如今还不到一年,已经是健步如飞,和正常人无异。
而我的舅妈,一辈子没怎么出过力的农村妇女,如今头发全白,身体里各种病痛折磨得她痛不欲生,我舅舅每天伺候她照顾她,算起来也不少年头了,能感觉到他对此事的厌烦。舅妈对每一个回去看望她的小辈们痛诉着她的不幸,儿子的不孝,后悔没有要个女儿,以及身体的各种痛苦,像祥林嫂一样,让人看了唏嘘不已。终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负担,谁人也无法代替,再多的苦难都要自己熬,命运使然吧!

输了舅舅这一生到底输掉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估计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这么多年他到底如何腾挪折腾得至今也没有欠下任何人外债。走在村里的大街上人们还是挺尊重他,我们这些小辈们,也就是他的这些外甥外甥女们分部在祖国的北上广深等地,每个回去的孩子都会去看望他,或多或少的买些礼品或是给些现金,而他总是很快的回馈给我们差不多金额的东西,或是蜂蜜或是木耳等特产,弄得我们很无奈。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你大舅这辈子谁的都不想欠”
我舅舅这一辈子虽然赌博,但是他没有拖累任何人,不管哪一个角色他都尽力去做好,做为儿子,他给父母养老送终。做为丈夫他伺候病榻上的妻子虽不够精心却也尽责。做为父亲,他对两个儿子也算掏心掏肺,扶上马送一程。做为大哥,不管哪个妹妹有困难他都出手相助。做为朋友,他的朋友临终之时抓住他的手托孤,可见对于他的信任。如果不是赌,他一定会是一个晚年还算幸福的老人,也或许不是娶了舅妈这样的女人,他一定是完全不同人生,可人生哪有如果,愿他所剩不多的人生能够幸福安康吧!

本文采自一位朋友的故事。
相关资讯